
三千多年前,商周之交,天下刚刚经历了一场动荡,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形下,周公旦却花了一年,闭门写出礼乐制度的雏形——将贵族的等级、祭祀的程序、朝廷的仪式、音乐的旋律都囊括在内。
当时,成王问周公:“为什么国家一乱,你先修礼乐?”
周公答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礼和乐,是国家和人心的根本。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立身之本。
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所谓“礼乐”,在先秦时指治理秩序、教化人民、安顿心性的一套规章。后来,周礼秩序瓦解,为恢复礼乐制度,孔子鲜明地提出,“礼乐”首先是一种为政之道,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外在规范,乐是内在情感的和谐。

《孔子》剧照
薛仁明是台湾知名的文化学者,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与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1993年起,薛仁明定居台东县池上乡,过着较为“隐居”的乡村生活,同时从事中学教育,并将自己的生命修行与中国传统文化重建结合起来。他长期致力于礼乐文明的当代实践,通过写作与讲座寻找当下中国人精神困境的解决方案。著作包括《教养不惑》《孔子随喜》《乐以忘忧》《其人如天》等。
在新作《教养不惑》里,薛仁明通过自己对三个子女的养育经验,特别强调 “礼乐文明”在家庭教养与生命成长中的作用,认为现代教育应回归传统文化中的根与气,从老祖宗的智慧中寻回一份温厚的从容与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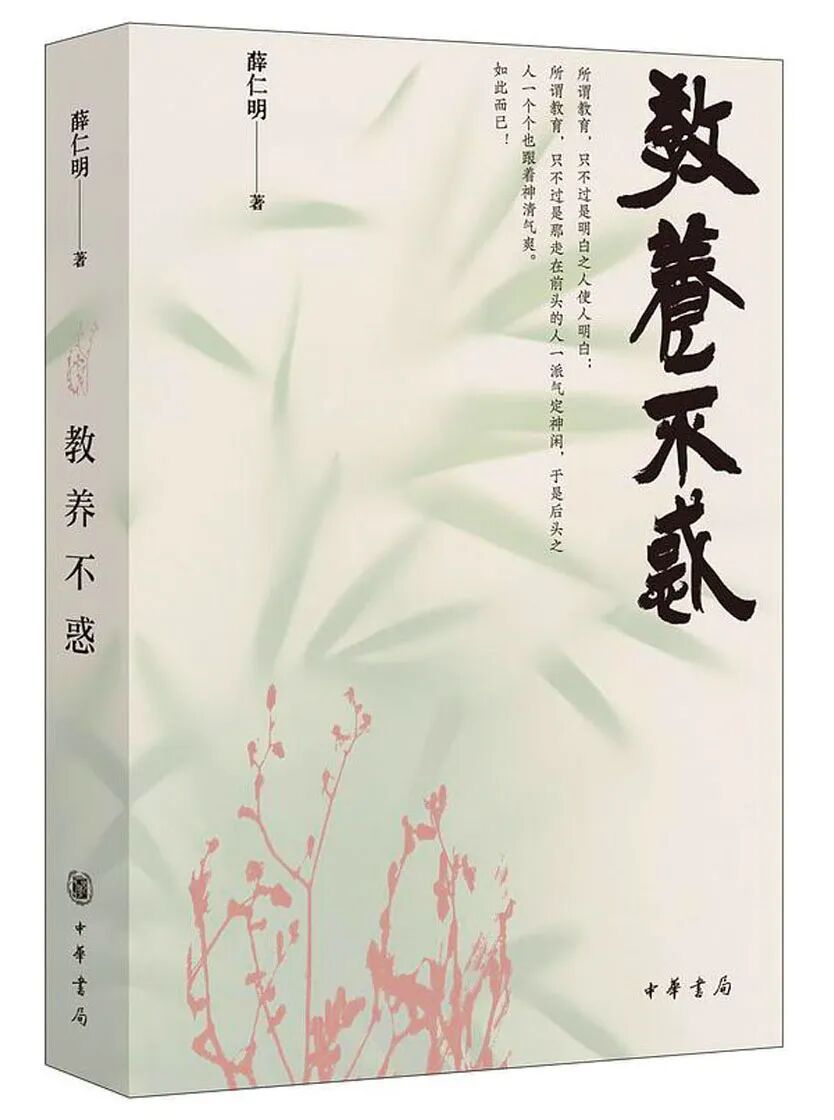
《教养不惑》封面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家庭,焦虑仿佛很容易贯穿教育的方方面面。薛仁明则认为,“难以养育”的根源并不在孩子,而在于教育者忽视甚至丢弃了“人应在其位”的文明框架。他所称的“礼乐文明”,并非复古口号,而是指恢复传统的秩序与位次,父在父位,子在子位,所有家庭成员各正其位,在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让亲人之间彼此信赖、包容,以达成更为融洽而一体的关系。
在与南风窗的访谈中,薛仁明从自身家庭经验与古典思想出发,对教育焦虑的起源、现代家庭的困局,以及文明深处的断裂,做出了冷静而尖锐的判断。

“去爱”就够吗?
南风窗:如今,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在家喜欢关上门,不愿意敞开卧室门与心扉与父母交流,这让他们无比烦恼。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薛仁明:今天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家长似乎没啥好抱怨的;说句难听的话,难道不是这些家长一步步把孩子推到那个境地的吗?首先,他们过早地让孩子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们误以为这有助于孩子的“独立”;接着,这些家长又过早地让孩子可以把房门关上乃至于锁上,因为,他们误以为这是“尊重”孩子、有助于孩子的“自我实现”。正是因为这种被误解成“开明”的想法,才会让孩子有了矛盾冲突之后,直接就理直气壮地把门“关上”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被误解成“先进”的做法,在孩子门关上了之后,家长只能自我绑架,束手无策地让孩子“率先进入”封闭乃至于抑郁的幽谷。
事实上,回到我们老祖宗礼乐文明的角度来说,只要把孩子摆在孩子该摆的位置上,这问题压根就不存在。今天之所以那么多家长深陷无力之困境,无非就是因为“错位”。

《小欢喜》剧照
南风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
薛仁明:这几十年来,中国父母过度想象了西方的“先进”程度,更高估了西方教育思维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可行性,因而蔑视中华优秀传统重中之重的礼乐文明,轻率地离弃咱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家庭范式。
试想:当咱们祖辈还在礼乐文明的框架之下,没几个人被“独立”“尊重”“自我实现”这些貌似“先进”的词儿给绑架之前,哪个父母会被孩子“关”在门外呢?从我们祖辈的角度看来,这种事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因为在礼乐文明的框架之下,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接近零。
事实上,西方教育不管是“以儿童为中心”还是“以人为本”的种种说法,无非是强调作为家长的我们必须去理解孩子、体会孩子、共情孩子。但按照这套理论实践下去,中国新一代的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被放置在一个总需要被理解的状态,因此很习惯别人必须理解他,但他并不需要理解别人。说得更直白些,他们只关心有没有“被看见”,又哪来兴趣、哪有空去“看见”别人呢?在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思路之下,久而久之,孩子会产生一个错觉:我是中心,我是我所在世界的中心。
这样的“世界中心”紧接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当他一到了幼儿园,就开始遇到了第一波撞击;等进小学之后,冲击便更全面而“严峻”。因为这孩子也是中心,那孩子也是中心;惯于唯一的“世界中心”的他们,自然就会觉得他们的“中心”地位被“侵犯”、被“挑衅”,于是就开始产生“人际关系”“情绪障碍”等等问题。以前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乃至于没读幼儿园就待在村子时,又哪来这么多问题?

《学爸》剧照
南风窗:在这方面,你是否观察到什么具体的例子?
薛仁明:我有某些学生的孩子读幼儿园,就因为人际交往挫折而不想去上学;而且不是偶发,是经常,甚至是长期。还有不少孩子幼儿园放学回来后,就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稍早之前的社会很少出现这种情形,过去的孩子看起来傻乎乎的,去幼儿园即便是不高兴了、跟人矛盾了,又哭又闹,过一会儿,也又能继续跟人家玩。他是有复原能力的,可现在这种从小成为中心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会因为人际关系而受伤很久,而且伤口还貌似永远好不了。才那么一点儿年纪,就搞得伤痕累累、终身需要“疗愈”。其实所谓“伤痕”,外表是谁把他怎么着了,但本质却是他被摆在了不该摆的位置上,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才导致的。
南风窗:为什么过去的父母觉得养孩子不难,今天的年轻人却常常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力不从心?
薛仁明:过去的父母,打小生活在礼乐文明的框架下,正如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宗一样,但凡吃得上饭、穿得了衣,养儿育女,天经地义,自然而然,哪有啥难或不难的问题?哪有谁觉得养孩子难到还得去上“家长成长”课程的?今天的年轻人,恰恰因为他们的父母轻率地离弃咱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家庭范式,“错位”之后,他们自然就缺乏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根基,再叠加那套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架构的影响,自然就容易有各种障碍、各种挫折,活得底气不足,面对现实的各种难题也缺乏咱们祖宗的那股劲头,于是他们就很难有能量,因此就更没勇气去生养孩子了。

把人放回“位置”
南风窗:你在多个场合都提过“礼乐文明的架构”。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薛仁明: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王朝有兴衰,文化有起落,但礼乐文明一直几乎是全覆盖,涵盖了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文明体系因而是特有的生活样式与行为模式。何以中国?其实,就是礼乐文明。所以,礼乐文明的架构也正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礼”是各正其位,万象历然;“乐”是山鸣谷应,一团和气。“礼”是父慈子孝,长幼有序;“乐”是路上有风景,人家有笑语。“礼乐文明”是有人有我,人我皆好。
《教养不惑》这书里提的两个关键字:简静。“简”是大道至简,不复杂;“静”是神思安安,不躁动。礼乐文明的架构之下,人世之间的确是可以这么“简静”的。我小时候就是如此,我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也大致如此,读者在此书读了他们仨写的文章应该也会有此感觉。事实上,我们祖辈自幼至长所受的教育,也一直都是这么“简静”的。

《中国》剧照
南风窗:在中西比较中,你特别强调“孝顺”。在“礼乐”的框架里,“孝顺”作何解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薛仁明:中国人之所以觉得孝顺是天经地义,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是“受之于父母”,父母生我有恩,养我有恩;父母之恩,终身难报。可是,西方人虽然也会尊重父母,但他们没有“孝顺父母”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是“受之于上帝”;父母先是“代孕”(代人格神上帝之意志而生孕),再是“托管” (代人格神上帝之意志而养育),等孩子成年之后,各自都回到“来自上帝”意义下的“独立个体”身份,因此,彼此本质上平等,所以相互尊重,孩子尊重父母,父母也要尊重孩子。换言之,父母子女的关系接近是平辈,因此西洋父母可以说跟孩子做朋友。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西洋父母之于子女,更多是“惠”,而不是“恩”。
可是,恰恰因为没有人格神上帝观的混淆,中国人很明确知道自己是“受之于父母”;也因为没有人格神上帝观的阻隔,中国人对父母天然有“亲” 有“敬”,我们很清楚父母“恩”重难报。换言之,中国的子女对父母一直有着清晰的“位”的概念。礼乐文明就是从这样清晰的“位”展开的。
南风窗:你如何看待现在流行的“生不是恩,养才是”这类说法?
薛仁明:早在约100年前,胡适之就对他儿子说“我养育你,并非恩情,只是血缘使然的生物本能。所以,我既然无恩于你,你便无须报答我”。相较起来,我们现在年轻人流行的“生不是恩,养才是”这种说法,显然敦厚得多,至少,都还承认养育是有恩情的,比胡适之有良心得多。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之其实是装没良心,因为,他只敢对他儿子这么说,你看他敢不敢对他娘亲这么说话?
紧接着,胡适之又对他儿子说“你是独立的个体,是与我不同的灵魂”。其实,他也不过是学着西洋人从人格神上帝观来说说话,倘使你真觉得他多么新潮、时髦,那也只能呵呵了!

《学爸》剧照
南风窗:你自己有三个孩子。现代父母最常见的情绪——“我怕养不好孩子”,你从没有过吗?
薛仁明:没有。我相信,我们的祖宗基本不会有“我怕养不好孩子” 的情绪,我也不敢有。现代父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无非是因为他们被 “思想殖民”了。中国人一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每个孩子的路就都不一样,只要我们把礼乐文明的框架确定好,孩子自然就会走一条相对合适的路。
西方人爱讲“普世价值”,又爱谈“唯一的真理”,结果咱们学着学着,都想走 “普遍而唯一的道路”,能不焦虑吗?西方个人主义强调个体、强调自我,还要让孩子去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我”;既然想“独一无二”,旁边的人自然都变成竞争、必须被排除的对象,那么,能不“鸡娃” 吗?
但是,“礼崩乐坏”都只是暂时的,礼乐文明不会真正消亡掉的。过去几千年都是如此,将来必然也会如此。正如人也会一时糊涂,昏了头,只要我们认祖归宗,很快就能回过神来。何以中国?礼乐文明。只要中华民族能伟大复兴,必然也会礼乐花开、天下文明。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马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