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北鸢》以提名前十的锋芒震撼文坛。
这部被读者称为“无冕之王”的杰作,早已横扫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央视“中国好书”等重磅奖项,更被陈思和誉为“新古典主义小说的定音之作”。葛亮以七年心血钩沉家族记忆,在《白鹿原》的苍茫、《繁花》的沪上烟云之外,以一只风筝牵起中国民间的精神脊梁——“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北鸢》如何以“无用之美”杀入茅奖前十?《北鸢》十周年珍藏版上市之际,葛亮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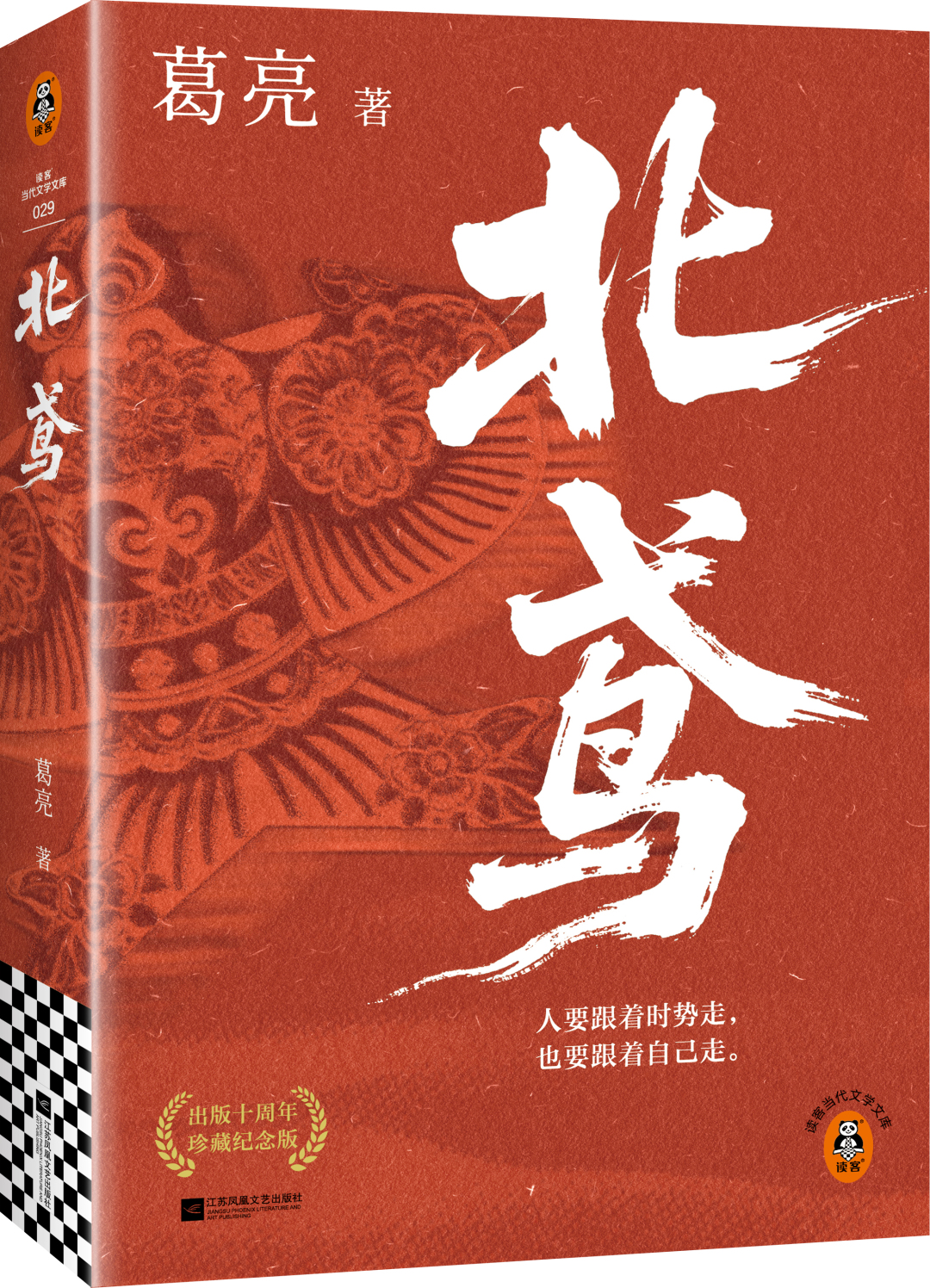
广州日报:今年是《北鸢》出版的第十年了,您的作品喜欢回望,那十年之后,您回望这部作品,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北鸢》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葛亮:我觉得十周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好像是弹指一挥间,但它留住了一个创作者的感受与回望。现在再看十年前的《北鸢》,我有一种犹望故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我会感受到那个节点上的自己。有时候这种回望也给你一个机会和空间,去重新认知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关照自己的来处。因为《北鸢》小说的主要脉络是关于我的家族,所以这个小说在田野调查的过程、写作的过程,包括现在回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发现自己、感受来处的过程,这是它对我最大的意义。
广州日报:《北鸢》这部小说您本来是想以祖父葛康俞为核心,完成一个关于家族的非虚构作品,后来却改成了以您的外祖父卢文笙为主角原型的虚构小说,从非虚构到虚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葛亮:最初是我祖父的艺术史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希望我写我们家族的故事。我准备了很多很多资料,整个准备过程非常投入。非虚构写作最大的压力是要还原现实中的这个人在历史中曾经身处的位置。虚构的好处是建构的轮廓相对来说是艺术的,而非虚构是历史的,需要极度负责。这对于一个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写作者——当时我大概30岁出头——是有一定压力的。
同时,在筹备过程中,我祖父一辈的亲友陆续凋零,包括范用先生、王世襄先生,他们去世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历史的轮廓突然之间就抽离了,这种抽离不是说少了一个去表达的对象,少了一个有关于历史的人的证据,它是一种情感的抽离。当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后来我选择了虚构的方式。
广州日报:大家对您的家世关注更多在你的祖父,而《北鸢》这本书的主角文笙的原型是你的外公,为什么当时选择写外公,而不是祖父?
葛亮:当你到了虚构王国,你想表达的历史要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共情。一个艺术史论家,和一个出生于商人世家的年轻人,两者周遭的天地、表达的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的天地是很大的。
比如他的父亲当年是李可染先生的赞助人,当时建了一间不收费的学堂,因为李可染先生的出身相对来说比较清寒,需要比较切实的帮助。李可染当时名叫永顺,后来就像小说写的,“孺子可教,素质可染”,给他改了名。在书里,文笙与克俞发生了一个相知的过程,其实在现实中他们不是师生关系。当然,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两个人除了艺术上的交流,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连接,一种薪火传递的过程。
广州日报:《北鸢》有给外公看吗?他看了之后有什么反馈?
葛亮:他有看过,他感到非常亲切。我的外公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从来没有希望我借此为他立传的心理。他是一个心态非常健康的老人,所以他把《北鸢》当作故事看。之前我其实也会想,他会不会觉得有些部分需要和事实吻合,或者说他会带上一种更加精准的眼光去看待他人生的节点。但是他的通达之处就在于,这部小说对他来说是一面镜子,他看到的人,是他,也不是他,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因为有的原型人物在看自己自传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甚至会提出诸多意见,但我外公没有,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因为我而有了温度。其实他的阅读观念,非常近乎于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审美的最高层级,是在灯火阑珊处的这么一个人。
广州日报:外公对你的创作、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葛亮:他给我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不会严格地界定自己对于未来的期待,所以每一道出现在他面前的风景,好也罢,坏也罢,都是一道风景。
我觉得我的外公跟我的祖父,对我成长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我祖父可能在治学、艺术观的角度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外公对我的影响更多是在人生观方面。
我的外公是一个平静而鲜活的人,用现在很时髦的词,叫情绪稳定,外公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我看到《北鸢》有一些读者反馈说,感觉仁桢更加灵动、更加活泼。好像文笙这个人性格一直都很温和。其实,他在重大的人生节点上,做的事是需要付出勇气的 ,但他是以最平静的方式做了这些事。
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跟我外婆吵过架,我外婆因为她本身的家世,她是有点性格的。在我的记忆里面,他们是性格非常不一样,但互相嵌合的两个人。
广州日报:书里有很多段爱情,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葛亮:我喜欢文笙和仁桢之间那种细水长流,彼此保持自己人生的独立,但是在重大的节点上他们相遇、相知,这是最棒的。
言秋凰的爱情太激烈、太跌宕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因为她是一个警喻之下的人,她的命运的悲剧,其实也是一种个体的悲剧,必须是那样一个人,才能成为那样的人。
在香港整个怀旧谱系里有一部蛮有代表性的电影,就是《胭脂扣》,我觉得关锦鹏导演在那个时代推出那样一部电影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它给予人的启示很多,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爱情观的碰撞。电影里面有一个片段,是编辑袁永定和他的女友楚楚的一段谈论,因为他们一起陪如花去寻找十二少,楚楚问他:“你会不会喜欢如花这样一个女性?”袁永定说:“我会更加喜欢你,她对我来说太激烈了。”楚楚说:“我还挺向往的,如果有十二少这样一个人让我去经历人生的大开大合,轰轰烈烈。”
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就是现代人对于爱情的一种讨论。它看似很日常,但其实也很严肃,有时候激烈是时代赋予的,楚楚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很可能就是如花那样的人。但由于她生活在现代,她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留给她的实际上是细水长流的稳定与日常。

广州日报:时代在变,有很多东西也是在变,但是有一些东西依旧是流淌在我们的骨血里不会改变的。您在小说中经常强调“常”与“变”,这也是《北鸢》这本书想探讨的主题之一,人在时代的变幻面前,应该如何自处。您在《北鸢》中其实也给了一个答案,就是说在时代的沉浮,人要顺势而为,但是不能丧失主心骨。您是认为什么是主心骨?
葛亮:在我看来,主心骨其实就是自洽两个字。你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时间点你要完成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心骨。
这是一个自处的问题。你在尊重时代变革的同时,也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尊重自己的人融入时代的同时,也在刻画着时代,我相信这也是“风筝”或者说“北鸢”这个意象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有了主心骨,你在一个时代里面走得越远,甚至在时代飘摇动荡、不安稳的这种过程中,你心里都有底气。就是所谓的“归家有时”,总归会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是我们的精神回到原乡的方式。
“归家有时”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来处,广义一点是寻根,抽象一点,就是寻找自己的某一个起点,当你发现无论是血缘的关系也好,还是家庭的关系也好,原来你的祖辈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是有源头,有来处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范畴上,他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当时写这本书,我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意义,就是它代表这种归家有时。归家有时,就像放风筝,不管你放得多远,它是可以回来的。当我在写自己家族的时候,我内心会有一种其生也晚的感觉,因为我是孙辈,跨得太远了。但是写的过程,我会感觉我祖父的那一代人,他所身处的历史语境与我越来越接近,是我在思想上寻根和回家的一个过程。我相信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过程,因为我把它分享给了广大的读者。
广州日报:你写《北鸢》的时候,提到老一辈的相继去世对你冲击很大,你会想要通过小说的方式来留存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吗?
葛亮:我觉得不是一个留存的意义,留存会让人觉得很感时伤怀,仿佛在挽救。其实我写工匠系列,最初是出于留存和挽救的考量,因为它跟我自己的非遗研究有部分重叠。但你谈到非遗,很可能就让自己堕入到某种思考的范式,很多东西可能要逝去了,但后来我真的进入其中后,感觉是非常愉悦的。而且工匠自身都不是这么想,不会说“我要式微了”“你要帮我留下来”“这个行业要走向末路了”,然后唱一曲挽歌。不是的,他们特别通达,他们对我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看清楚了所谓的新与旧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它不是一个我存活不下来,要让诸多的外力去帮助我留存的这么一件事,而是每一样新的东西都会变成旧的,然后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也不是壁垒分明,旧的东西可以融入新的东西里面。它作为一种基因也好,作为一种血液也好,它帮助新的产生了更新的,生发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给我最大的启示。我写小说其实是想把这些有意义且微妙的部分表达出来,而不是唱挽歌,我不希望说我的作品好像是一个前朝遗少写时代遗存,不是这样的,我要借此声明这一点。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吴嘉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