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茗婷
编辑 | 赵靖含
老街角,杂货店。黑长直,麻花辫。
蓝衬衫,落泪脸。小县城,旧情人。
大概是从五一假期起,顺着“反向县城旅游”的走红,一组以县城、小镇为背景,以泛黄的怀旧风格取胜的人像写真或街头摄影,被推到大众视线内。
人们将这种风格称为“县城文学”,继“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发疯文学”之后,它再次搅动互联网一池流量。某网络社区上,“县城文学”的话题浏览量超1600万,而相关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则达到4.2亿。
“河南说唱之神”在5月9日发布了作品《工厂》,它包含了一首回看故乡的歌曲,一部在焦作拍摄的MV,一个将村庄碾压为脚下瓦砾的坍塌过程。高赞评论说,“这才是真正的县城文学”。他唱“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唱出了无数从县城出走的游子的心声。

《工厂》MV截图
他们从县城走出,漂在大城市,成了无名之辈,化作大数据的分母。城市很大,却容不下他们;想回家乡,却心有不甘。
县城文学,有乡愁的内核,也有个体叙事的疏离。
这一场互联网自发的碎片式创作,无论是否能被真正冠以“文学”的名义,都确确实实将县城推到舆论场的中心。
向前溯源,我们会发现,县城其实从未在当代文艺创作中缺席。从1980年代在县城落地生根,到1990年代对县城感到彷徨,世纪初时初见城市微光而逃离县城,如今再回望县城,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生命经验哺育了县城文学的创作。
文学与影像,始终与县城的进化和人口的流动亦步亦趋。
01
在县城,看世界
1986年,作家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开始在《花城》杂志上发表。
这是关于一个贫苦青年从农村出走,到县城里求学、工作,像牛马一样咬着牙忍受劳累和被生活和命运锤炼的痛苦的故事。
县城,比黄土山沟里的小村庄宽广、丰富、精彩得多,那有剧院、法院、银行、工厂,是孙少平的全世界,容得下一个小人物的梦。兜兜转转,他最后以煤矿工人的身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袁弘饰演的孙少平
孙少平的故事,也有路遥人生的痕迹。“农民的儿子”路遥,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曾因为出身贫寒而差点辍学,在乡亲的托举下,他才得以进入延川县城的中学继续学业。
成为作家后,他继续偏安黄土高原一隅,忍受贫苦、寂寞与病痛的折磨,用纸笔创造了《平凡的世界》这样一本文学巨著,以一名农村人的奋斗丈量人类精神的宽广。
跟路遥一样,县城是很多人观察世界的起点。
1997年,汾阳小子贾樟柯,完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业后,回到故乡县城,将镜头对准了一名随处游荡的闲散青年小武。
小武偶尔借钱,惯于盗窃,总是发呆,很想恋爱。伴随着人物游荡而出现的,是县城脏乱的街道,迷幻的歌厅,破落的砖墙,逼仄的民居。这样的人,是真实出现在贾樟柯生命里的小偷朋友,他们也同样出现在你我的县城生活中,是从小学习不好被留堂的同学,是长大后的整日走街串巷的街溜子、小混混。

《小武》剧照
如果说,路遥笔下1980年代的县城,给予了孙少平实现阶层跃升、开启人生可能性的故事,那么贾樟柯镜头里,在1990年代正在剧烈转型的县城,则是一种人的隐喻,小武是县城青年们在跟不上环境发展的写照,是受到外部冲击的而逐渐崩塌的传统社会关系。
前者,被县城接纳,是昂扬的叙事,是个人奋斗的华章。后者,被县城抛弃,以念旧的心态频频回望,却无力改变。
叙事基调的不同,取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同向同步,还是背离抛弃。但不变的是,县城一直在前进。
02
电影里的县城
1998年,《小武》让汾阳小子在世界影坛大放异彩,之后,贾樟柯继续对准着县城的太行山脉、滔滔黄河和边缘个体,在21世纪的头15年,他陆续创作了《站台》《天注定》《任逍遥》《三峡好人》等作品。
这段时间,也是城镇化的列车加速前进的时期,2000年之后的十年间,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一半人口已经完成城镇化的转型。

《天注定》剧照
在这场农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动迁徙之中,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本单元、乡土中国往现代化国家的过渡地带,县城往往承担了执行者与中转站的功能,机器轰鸣,车流不息,人口复杂,县城面貌多样而复杂。
现实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多样的素材。有一批人像贾樟柯一样,用影像忠实地记录着或主动或被动逃离乡村和县城的故事。他们共享同一个名字:中国第六代导演。
地理特征往往是建构影像与文学的重要元素,与以对准黄土地上生死疲劳的乡土故事的“第五代”的不同,对于“第六代”来说,县城复杂繁茂的风貌为他们的叙事提供了核心意象。
伴随着电影背景从乡到县的推移,这一代导演的创作母题,从家国同构下的乡土寓言,转入到边缘个体迷茫。
似乎是历史的巧合,当下网络“县城文学”被人讨伐的命运,也降临到第六代导演头上。当他们用镜头对准县城城镇化建设下个体生活的流离、精神的迷茫、环境的封闭落后,这种创作风格曾被人批评为个人经验的局限、以“审丑为美”。
但这种创作风格来源于作者对时代的强烈敏感贾樟柯说:“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气息,因为整个国家、社会都在一个莫名巨大的推动力下飞速地发展,人们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他镜头下的汾阳,“每天下午都有浓烈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正是从这里出发,巧巧、斌哥、韩三明,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所裹挟着前进,三峡县城的时代家园被时代洪流淹没。

《任逍遥》剧照
同样是三峡边上,在“第六代”导演章明的故乡巫山县城,常年被从长江升腾而起的水汽云雨覆盖,像冥王星一样被人遗忘,但边缘的处境阻挡不了江城青年男女自发的欲念,像连绵崇山里的植被一样,蠢蠢欲动而富有生命力。
王小帅镜头里,父辈为建设背井离乡在贵州县城扎根,而“青红”们则通过离开闭塞无序的县城,逃离命运、代际和爱情给她造成的伤害,渴望在城市的繁华中流放和治愈心灵。
时代走到这里时,人口流动的坐标系已经形成了乡村—县城—城市的顺序,“青红们”的故事,将县城叙事延续到北上广的浮华和大城市的开放中。
03
逃离与回望
逃离县城,一度是县城有志青年们的宿命。具体到这群以“70后”为主的“第六代”导演身上,他们大多拥有一个标签:北漂。
贾樟柯说:“我真正获得故乡,其实是因为离开了它。”章明的单位和户口都是北京,但他说:“北京好像跟我都没什么关系……我始终没有把北京当成我的一个故乡,我永远觉得是一个客居者,总是回到巫山的时候才会有一种亲切感。”

《青红》剧照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乡愁,寻找归属感,漂泊在偌大、冷漠的城市里无所安定,却频频在城市里回望家乡,在影像里重塑故乡。
世纪之交,城市化如同铁军强旅一般在华夏大地上攻下一段段进程,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起,互联网铺开,超级城市崛起。以制造白日梦为基调的网络文学,遵从了资本逻辑,通过网线与无线通信走到台前。
越来越多从县城逃离出来的人,加入网络文学的创作。以80后作家为主体,不再写县城了,要写城市,写光鲜靓丽、纸醉金迷的城市,“青春文学”的概念浮出市场。
2003年,一名出身自贡富顺县城的作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幻城》,一时引人瞩目。至此,这名来自小县城的、身材矮小瘦削、此前无人知晓的作家,一夜天下知,他就是郭敬明。
2008年开始,郭敬明的文学商业帝国随着《小时代》的出世而向上走,如同郭敬明的小说所反映的那样,时代与世人纷纷将注意力挥洒给了城市,现实主义县城叙事,沦为了小众的品位。

《小时代》剧照
但还有人在坚持记录县城。与郭敬明、韩寒等同为“80后”的作家孙频,坚持在记录小城故里的人们。孙频同样来自山西县城,位于吕梁山区里的交城县,自隋开皇十六年置县以来,已有千年历史。
孙频对小城的记忆,总离不开女人的谩骂声和苹果腐烂的味道,那么尖锐,那么浓郁,那是她成长过程中的一则邻居往事,也是残忍生活对世间万物的痛苦产物,辛辣鲜爽。
2008年,孙频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第二年,她在太原日复一日的痛苦绝望中开始写作,她忠实地记录着山民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都市,而后又折返的故事。她将“山林三部曲”,称为自己对“故乡的重新发现”。
《以鸟兽之名》里,在县城扎根的主人公,永远失去了故乡和童年。《天空之城》里的工厂子弟,突然降临的纺织厂,是城市化的象征,冲击了县城的平静生活,新旧交替之间,个体离散,无处扎根,内心不安。而后的“海边三部曲”,她走出太行山脉,来到最南端的小镇,但不变的,是她继续书写着那些在大城市、小县城、老村子之间游走的青年男女。
孙频说:“我对时代夹缝里的人物充满兴趣,他们……险峻、幽僻、孤寒、不乏狼狈,如一根针深深嵌进时代的肌理中。”而县城,何尝不也是在乡土格局和现代化进程的夹缝之间生长发育的生命?共2844个大大小小的县级行政区,散落在半个中国版图的各个角落,长时间来努力地向外吸收、自我发育,他们也像那些边缘小人物,等待着时代与命运的呼唤与召见。
04
重 返
如今,时代的重任已落到县城头上。2022年,一纸政策文件落下,县城成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随之而起的,是县城叙事的重返舆论场。
“被热议的县城贵妇”“北漂青年被县城生活穷笑了”,将县域经济的强劲消费力摆在了台前。各大品牌纷纷下沉到县城设店,星巴克,覆盖中国超800个县城,而类似的跨国集团与一线品牌,将县城视为蓝海市场,趋之若鹜。“县城婆罗门”、县城体制内剩女、县中坍塌、县乡中国等学术议题,让界视野对准县城这片田野。
具备高度统一的创作特征的“县城文学”在互联网当道。人物的清冷气质,彷徨神态,倔强眼神,带着破碎感的回眸和流泪。人物眼前是凋敝、破落、残旧的县城街头。“走不出,看不破”“带我走好吗,离开县城”的文字,是悲凉伤感的基调。
这些日常的元素,是这场互联网狂欢的文化基因,构建了一组高度同质化的模板公式,人们只要通过模仿便能轻易复制生成。
他们穿着褪色的蓝衬衫、复古的红裙子,拿着卡片机、CCD、胶片相机,纷纷涌入县城,拙劣地模仿着贾樟柯和王家卫的影像风格,或高饱和,或褪色,拍出胶片感,打卡、拍照、发朋友圈,以相似的景观和情绪氛围,拼凑了他们想象中的县城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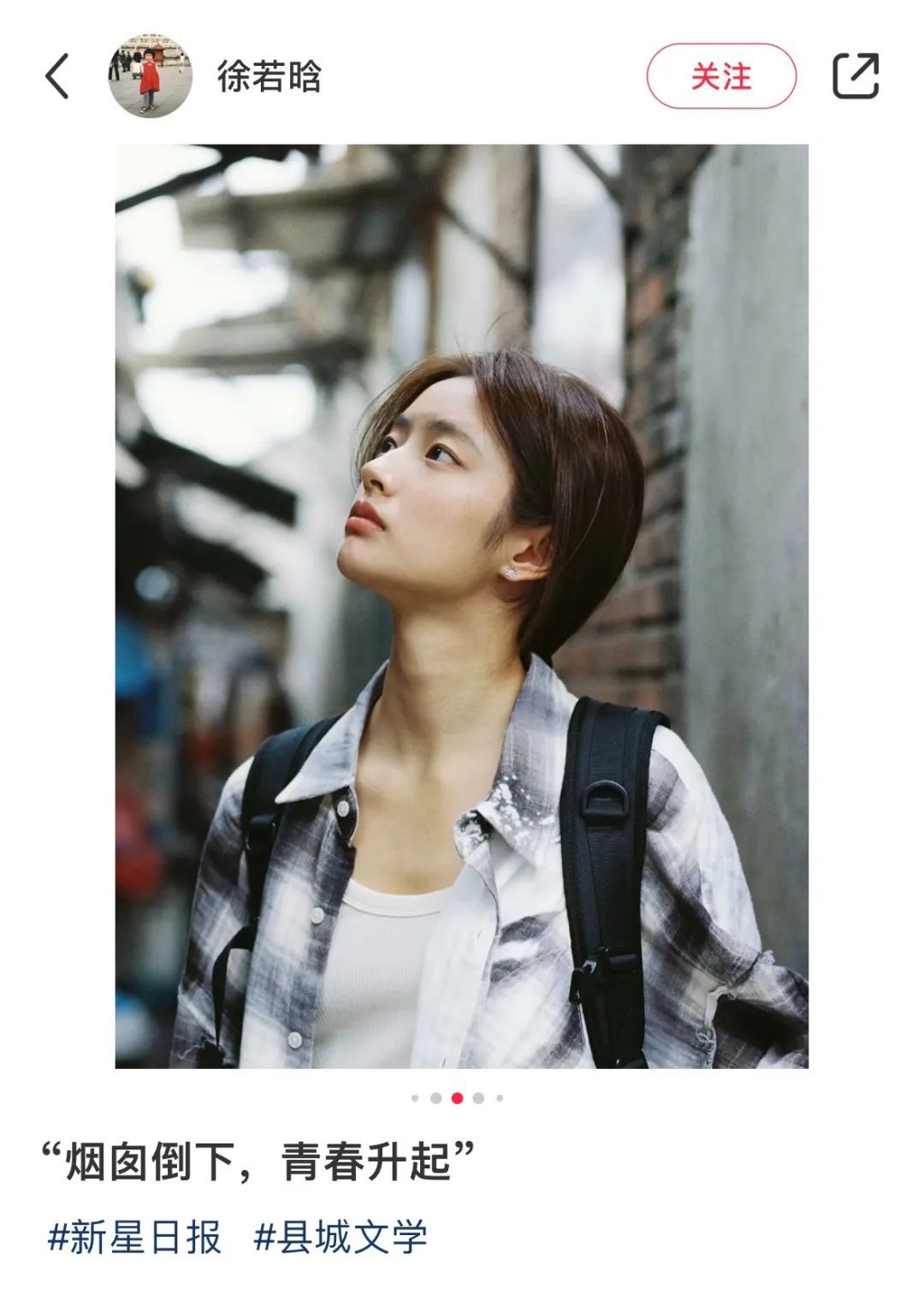
演员徐若晗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县城文学”写真
用居伊·德波的话来说,“景观不是影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延展到现实生活,便由外部环境、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内心情感交织而成。这些是故事的基本要素。这可以解释为何当下大众常用“故事感”来评价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否足够吸引人。相同的评价也出现在“县城文学”的文化现象之中。
追逐“县城文学”的人,被其中的怀旧风格,人文烟火气和写真里人物伤感却坚毅的眼神和破碎与韧性同在的人物氛围所打动。
但“县城文学”也招惹了生活在县城的人。他们认为,“县城文学”废旧的城市图景,抹黑了自己蒸蒸日上般发展着的家乡,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家乡对标一二线城市的发展细节,细数自家附近的奶茶店、咖啡店,商场里的高端品牌等,以显示当下县城生活的时尚、便捷、安逸。
一边是现实世界里县城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靓丽,另一边是赛博世界对县城凋敝尽情想象的文化狂欢。而无论褒贬,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心态:如今我们在怀念县城,也在向往与拥抱县城。

《天注定》剧照
现代化的千军万马碾过县城的土地,掀起的漫天尘土模糊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个体。幸好我们还有文学,有电影,可以将这些面目模糊的个体,将他们的身形和轮廓从生活的洪流中打捞起来,在文艺的世界里将这些鲜活的生命复刻、描摹、记录、保存。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1期
-END-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排版 | 起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