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靖芳
演员陈瑾在出演电影《吾爱敦煌》中的“樊锦诗”时,曾经感到压力很大,几度想要放弃,“你跟她越接近,就越觉得够不着她。”
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的一生,心归敦煌,守候在戈壁守候莫高窟的故事,如壁画般的浓重瑰丽。近期在院线上映的电影《吾爱敦煌》,把樊锦诗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在我们眼前。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莫高窟南区准备启动加固工程,正需要一些专业的考古学生协助发掘。
对于年轻的考古系学生来说,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艺术宝库,人人心向往之。
当时24岁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被选中前去实习。初次进入洞窟,温度比室外还要低得多,樊锦诗看着洞窟里色彩斑斓的壁画,把寒冷忘记了。从北魏到隋唐,从女娲到飞天,满天的壁画犹如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

图为1964年,樊锦诗(左一)在敦煌工作
上海长大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虽然满心欢喜,但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实习结束后,当她被正式分配到敦煌工作后,但父亲担心她的身体,写信给学校领导希望改派分配。
樊锦诗偷偷拦下了这封信,她不希望搬出父亲来说情,她接受了分配决定,“说不定这就是天意”。孤寂辽远的莫高窟长期被风沙包裹,见证着一代代为它而来的人。在毕业后的55年时间里,樊锦诗远离了繁华又喧嚣的都市,在大漠里成就自己的事业。
《吾爱敦煌》讲的不仅是樊锦诗,也不仅是敦煌,还是当下社会里稀缺的人物画像。整部片子看完,让人感受到少有的平静,回味久远。
01
用笨方法来传承
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洞窟的分布高低错落,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公元366年,一名僧人路经鸣沙山,看到这里有金光闪耀,于是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
多年之后,丝绸路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在当地上任的官员、百姓、财主、绅士为了积功行德,都纷纷来开凿佛洞、塑佛像、画壁画,一个个洞窟营造起来,从无到有,千年的时间里,这片断崖成为了万佛之国。

敦煌莫高窟
常年的风沙洗礼,带给了莫高窟独特的历史面貌,也塑造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樊锦诗有过敏性鼻炎,所以经常带着手帕擤鼻子,她初到敦煌时,就有前辈提醒她,这里工作的人大多患有鼻炎,因为莫高窟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我们门窗都不严实,外面刮风,屋里下沙子。”
樊锦诗在自传里回忆最初住的房子,天花板是用芦苇秆搭起来的,咚的一声,晚上还会掉下来一只老鼠,“冬天零下二十多度,怎么办呢,有时候就吃辣椒,大家跳啊什么的。”用这种办法来应对严寒。
第一代敦煌人来到莫高窟,最先解决也是风沙问题。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来到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并开始修建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但是,敦煌没有土,只有沙,很巧合的,他在商贩那里学到方法,“用含碱量大的水混合沙土,使劲夯,就能筑成墙”。
有了这堵两米高的土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就这么笨拙但仔细地展开了。
莫高窟周围,围绕着一代代的工作者:他们是修文物的人、讲解员、技术人员等等。在他们到来前,莫高窟不过是一片沙土堆积的断壁残垣和危险楼阁,人们随意地在洞窟里夜宿、烧火做饭,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保护和修缮。

《吾爱敦煌》剧照
融合了中国和西域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莫高窟,被如此冷落在荒凉的境遇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常书鸿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亲自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的年轻人。
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是常书鸿的学生。后来,也有“门外汉”来到。
《吾爱敦煌》的讲述里,少年的樊锦诗在洞窟里碰到了工匠李云鹤,林永健饰演的李云鹤告诉她,自己原本是一名山东青州的农民,带着几个伙伴准备到新疆种棉花去,路过敦煌,想到莫高窟拜拜菩萨,结果遇到了常书鸿。
常书鸿一再劝说,把他留了下来。
李云鹤干活勤恳,他原本以为在莫高窟的工作是一些体力活——把洞窟里的积沙扫出来,堆到窟崖下面,再用车拉走;这些工作他干起来很勤快,但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打算交给他专业的修复保护工作。
年久失修的莫高窟壁画表面,出现了起甲、空鼓等现象。起甲是壁画上出现了像鱼鳞一样的龟裂,空鼓则是因壁画和墙面之间存在空气,敲起来有咚咚的声音,两者都算是“病害”。
外国的专家为此专门来过莫高窟,在现场演示了一种“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很适合壁画的修复。

林永健在《吾爱敦煌》中饰演李云鹤
李云鹤在旁边观察得很认真,专家走后,他试着用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制成黏接剂,再用针管顺着起甲壁画的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进去,等到壁画表面水分变干,他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确保粘贴得牢固。
当时,国内对莫高窟这样的洞窟进行壁画修复的科学方法,仍是一大片空白——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是李云鹤在往后的数十年里边摸索边改进:针管太粗了,他换成气囊;纱布有纹路,他改成了纺绸,在这样的探索下,李云鹤逐渐成为了著名的壁画修复专家,成为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
樊锦诗在自传里感慨地说,“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边干边摸索”。
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宿命感,樊锦诗沿袭了这样的心性和精神,她也跟着走上了保护莫高窟的道路。
02
为了留下莫高窟
樊锦诗最初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的老师——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对她寄予了一个希望:完成莫高窟的考古报告。
古代的文物遗迹历经久远,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发掘保护下,它们能延长寿命,但很难阻挡其退化的趋势,莫高窟也不例外。
“即使有一天石窟不在了,人们也可以根据考古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石窟进行精准复原”,这是考古学界人士对莫高窟考古报告设立的祈愿。

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
在另一部名为《敦煌师父》的纪录片里,记录了敦煌研究院里的师父和徒弟们的故事。其中一集的主角是浙江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张小杨,她是考古研究所的新一代年轻人。工作里,她被分配到完成第254窟考古报告的任务。
这个任务难倒了她。考古报告需要对洞窟整体结构和所有壁画细节进行详细记录,254窟是莫高窟开凿时间较早的洞窟之一,壁画存在着烟熏、脱落、破损的问题,很多地方模糊难辨,何况,“一千个形态不同的佛菩萨,就要经过一千次辨识、考证与记录。”壁画烙下了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风格,需要记录者耐心地了解和厘清背后的历史意义。
单是一个洞窟的考古报告的困难程度是如此,整个莫高窟考古状况的难度可想而知。

纪录片《敦煌师父》截图
实际上,还有一个难关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樊锦诗没有真正想明白考古报告应该怎么做,她毕业多年,但仍觉得没学透宿白先生的学问。编写考古报告的过程中,她经常向老师请教、询问,却没有如愿得到老师的认可。
后来,她发现莫高窟的考古不能照搬普通的调查方法,一般的野外调查工作,都用手工测绘的方法,但是莫高窟是一个个曲面的洞窟,壁面与壁面的连接处不平整,造型复杂,而且塑像之间不在同一个方位。也就是说,传统的测量和记录方法很难把莫高窟洞内的情况记录详尽。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樊锦诗改用了三维激光扫描仪,用当时先进的三维技术测绘出精准的数据,终于达到了考古报告所要求的准确度,也得到了宿白老师的认可。
2011年,樊锦诗73岁,在敦煌守候了49年后,她和团队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一共780页。
这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既是一份科学的档案,也是敦煌人对后世的一份责任感,樊锦诗认为,“要用历史的态度看考古报告,它不仅是给今天读者的,也要流传后世。”
为了能长远地留下敦煌的影像,樊锦诗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想法。那时候,数字化还是很前沿的想法,人们只习惯用照片、档案的形式保存文物形象。

彩塑三维重建艺术复原成果
但现实是文物在逐渐退化,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已经发现发生了很大变化,壁画多年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
20世纪80年代,樊锦诗然到北京出差时接触了电脑,倒腾半天后,她没懂:“关了不就没了吗?”别人跟她说,只要变成数字,就不会变了。樊锦诗受到启发:变成数字就不变了,能放大能缩小,那能不能做我们壁画?从此,“数字敦煌”在樊锦诗的心田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设轨道进行移动拍摄,再进行图片的拼接,探索的道路逐渐走上了正轨,接近20年后,敦煌研究院才做成了高保真的数字档案。
“数字敦煌”的构想,还包括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这个像电影院一样的装置同时还平衡了庞大的游客数量带来的影响。
莫高窟的洞窟大多空间狭小,壁画使用的是泥土、麦草和木料等等材料,质地脆弱,日益增加的游客难免会改变的洞窟湿度和温度。
经过推演和研究,游客如果能先到展示中心观看电影,既可以了解莫高窟历史,又能适当减少看洞窟的时间,这样的动线让接纳游客数量能增加到每天6000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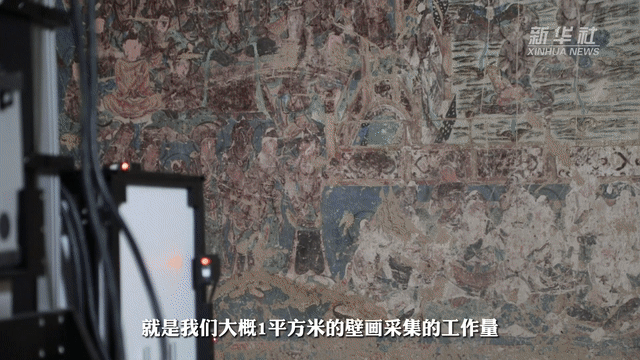
敦煌研究院数字化团队 / 图源:新华社
2016年,“数字敦煌”上线,这意味着可以将莫高窟人类文明的结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说,这项工程,“是与时间赛跑,有抢救文物的意义。”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两年时间想这个事。”樊锦诗四处奔走,为的是“数字敦煌”能让敦煌文化走出去,活起来。如今,她能颇为自豪地说道,“现在据我知道小孩都知道在手掌上可以看敦煌,随意地去点,随意地导览。”
03
相依相偎的一生
常年与敦煌的大漠相伴,樊锦诗已经习惯了莫高窟偏远的生活,但在这里她远不孤单。因为,她还有一位相互依靠的伴侣——老彭。她形容自己和丈夫彭金章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两人是就读北大时期的同学。毕业分配时,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得知自己要去敦煌颇为犹豫,但那时候她想着,先去一段时间,“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还是能去武汉。”分别的时候,她没想到这个间隔是19年。
面对分离,是莫高窟人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也伴随着最挠人的痛苦情绪。樊锦诗在传记里回忆说: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

樊锦诗与彭金章
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开创的是新的学科事业,由他带头,武大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教师队伍。
忙碌的夫妻每个月都会通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在樊锦诗的文字里,老彭是个可靠又细心的丈夫。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敦煌医院的护士帮她往武汉发了加急电报。老彭带上了两个家庭准备的奶粉、衣服等各种东西,担子装得像个“百宝囊”,他把所有的行李从武昌挑到敦煌。路上10天的时间里,担子里的鸡蛋,一个都没有碎。
因为两人没有带孩子的经验,老彭还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里面教会了新手母亲要多长时间给孩子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有这本书的帮助,樊锦诗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1986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老彭决定离开武大,调到敦煌。在敦煌,他的考古事业没有停下来。莫高窟北区的石窟考古,是敦煌研究所成立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彭金章主持了这项工作,他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
更为重要的是,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停不下来。也就在老彭调来敦煌的那段时间,樊锦诗一家真正团聚了,两个小孩虽然在兰州上学,但他们利用出差的时间能经常见面,“这个家就像家了”。
两个相互为考古事业贡献了一生的真挚之人相遇相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简单,却又让人动容。可惜的是,2017年老彭生了重病,随后不治离世。这对樊锦诗的人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依赖老彭极深,并且对丈夫充满了感激,她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樊锦诗与彭金章
老彭离开后的日子,她一直觉得他还在。有一次别人给她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她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
电影里,樊锦诗和老彭的故事更为真挚,平淡的相守到了荧幕前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樊锦诗的工作一样,她的感情、生活也在敦煌里飘荡、交织,成就了她独一无二的经历。
让人确信的是,大漠的日子里,樊锦诗愈加相信自己是必然要来到莫高窟的人。外界所描述她的这些片段,远远无法构筑理解樊锦诗的全部,《吾爱敦煌》也只是给观众揭示了她人生里的一角。

《吾爱敦煌》剧照
樊锦诗在莫高窟待的时间越长,越想起她的同行前辈们。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他们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这个单位和他们不一样,是在戈壁沙漠中,大学生、留学生在这里坚守,这不一样。”
但樊锦诗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之事,“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电影完毕,这一幕场面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莫高窟一直在等着,那些必然要来到它身边的人。”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ND-
编辑 | 吴擎
排版 | 风间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