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漄获得雨果奖,让《银河边缘》这一原本在主流文学杂志之外显得有些“边缘”的科幻书系,走到了大众视野中。
田兴海是海漄的责任编辑。他与海漄之间,颇有点“伯乐与千里马”的意味。早在湘潭读大学时,同样也为科幻作者的田兴海,就通过一个科幻作家群认识了海漄——那时的海漄曾于2012年前后零星发表过几篇文章,随后因工作等“搁笔”许久。直到2018年田兴海入职八光分开启《银河边缘》系列,在找中文科幻作家约稿时,他联系海漄,问道“要不要试试创作科幻小说”。看到有新平台诞生,海漄也立马应承下来,并从2019年起陆续交出《血灾》《龙骸》《时空画师》等多部作品。
获得雨果奖后,海漄开始像星星一样“发光”,但在走近《银河边缘》的过程中,记者却发现了故事的另一个视角:它关于“雨果奖”得主背后的一群人,或许他们才更贴近中国科幻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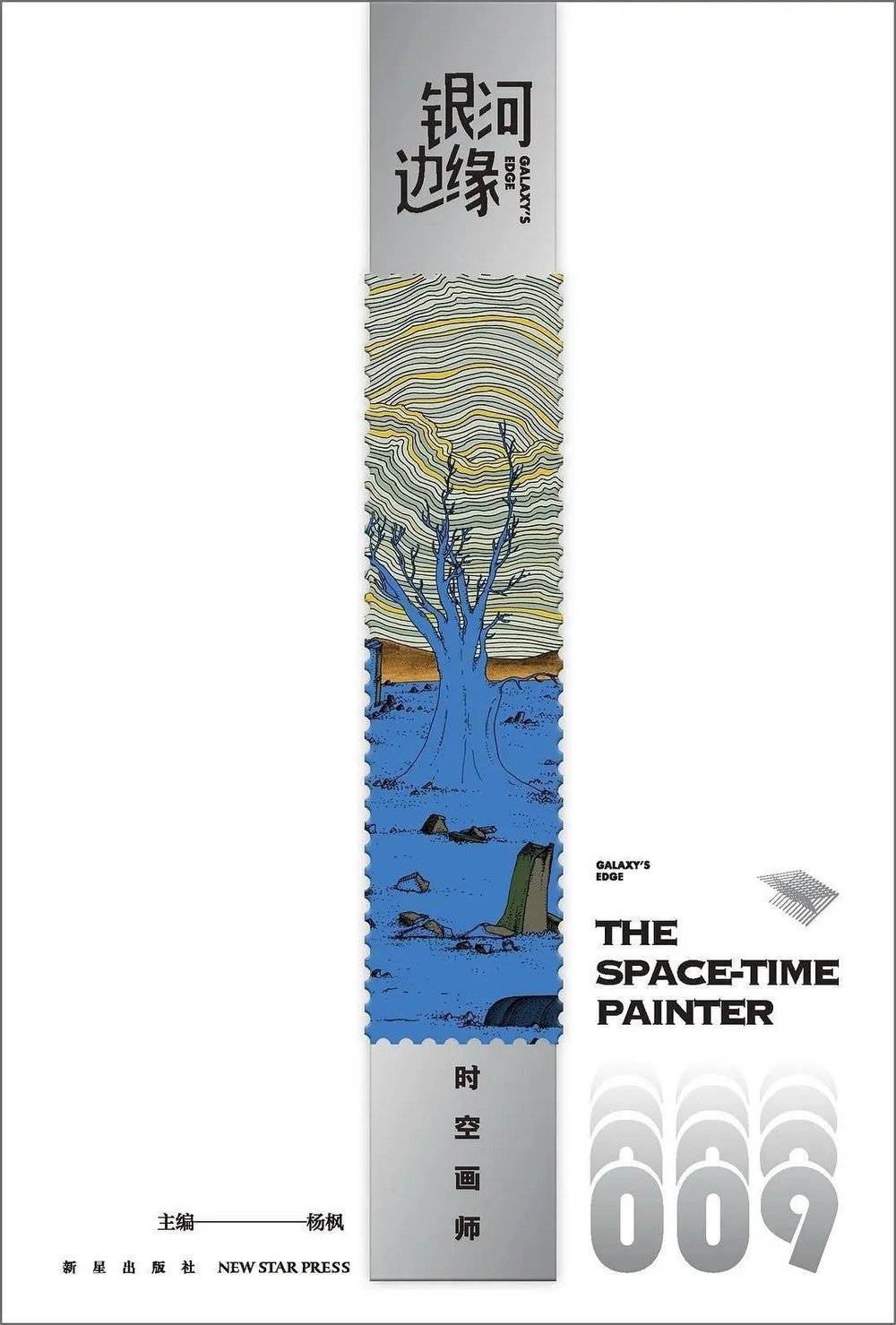
时空画师
与《银河边缘》编辑部对话时,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一部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
他们与《宇宙探索编辑部》有太多的相似,
比如规模都很小,只有几人;
编辑部的生存空间不大,在《时空画师》“出圈”前,《银河边缘》也曾经历过更换出版商、发行周期不稳定等“坎坷”;
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理想主义内核,热爱科幻,并孜孜不倦地发掘中国科幻的可能性……
但不同的是,在这个残酷的图书市场中,《银河边缘》得以存活下来,并孵化出一部“雨果奖”作品。采访时,田兴海发出如此感慨:
“幸好我们坚持了,否则可能大众就看不到《时空画师》这样的作品了。”
一个几人小团队:
“《银河边缘》是个艰苦的项目”
 杨枫
杨枫
《银河边缘》的创立,背后离不开一个人:杨枫。
杨枫是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创始人之一、“冷湖奖”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科幻世界》杂志的原副主编。2016年从《科幻世界》离开后,杨枫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了“八光分”。但与大部分着眼于科幻IP影视或衍生品开发的创业公司不同,杨枫选择了以传统的图书出版为主业,“因为这是中国科幻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基。”杨枫说。
两年后,这家规模当时还不足十个人的初创公司很快在中国科幻界发出了声响——《银河边缘》中文版诞生。
《银河边缘》原本属于美版杂志,2017年底,在获得了中文版权后,《银河边缘》以一种“中文原创+英文译作”的组合方式引入国内,成为在中国发行的科幻文学读物。倘若你仔细翻开《银河边缘》第一辑到最新一辑的目录,就会发现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新人作家不断出现;二是中文科幻小说和英译名作的占比,从起初的1:4逐渐变为5:5——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数量增加了。这正是杨枫当时出版《银河边缘》的初衷,“中国科幻宇宙里,不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颗星星,《银河边缘》就是为新人而生的。”
但这也注定了《银河边缘》的不易。在科幻产业体系里,阅读、影视、游戏、衍生品四大板块中,科幻阅读板块的总体营收实际上是最低的,涨幅也是最小的。今年3月28日,《银河边缘》创办四周年之际,执行主编戴浩然就曾在《银河边缘》创办以来给读者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犹记得(几年前)刚入行时,许多出版社哪怕出的是科幻小说,也绝不会轻易打上科幻的标签。如今科幻虽然不再是入行当初的各家弃若敝屐之物,且科幻话题越来越热,但实际上科幻小说的发表平台却锐减,尤其是中短篇科幻小说……而我们八光分始终觉得,中短篇科幻小说的故事特性,还是更适合印成铅字,这就是《银河边缘》坚持的原因。”
“《银河边缘》从开始就是一个极其艰苦的项目。”在采访中,田兴海也感慨。事实也确实如此,五年间,《银河边缘》就经历了更换出版商、出版周期不稳定等诸多不易,“不过最大的不易还是组稿。”田兴海透露,尽管科幻近些年成为热议话题,但科幻小说创作的热情实际上还是比较弱,虽然也有一定的来稿量,但并不是非常庞大,“尤其《银河边缘》是为新人而生,也更倾向于多出新人的作品。主编杨枫又是一个对于文稿要求非常高的人,因此每一期的《银河边缘》都得经过千挑万选。”
如今,经过将近五年的坚持,《银河边缘》已连续发行15辑,不仅诞生了如《时空画师》这样的作品,还孵化出如“星云奖”金奖作品(梁清散《济南的风筝》)、宝树《天象祭司》)、冷湖奖一等奖作品等,让包括海漄、陆秋槎等科幻新人也都拥有了被看见的机会。
正如《科幻世界》编辑、著名作家谭楷曾在《中国科幻口述史》中给“八光分”写过的一段话:“你不停地带着星星旋转、飞翔,给它们力量,给它们光和热……于是,你像看不见首尾的大队伍,闪闪发光,在浩渺星空中走过。”杨枫和她的团队就是这样一群点着火炬,在宇宙边缘点亮星星的人。
谈海漄及其创作:
“他是一个极为自律的作者”

田兴海(左)
如今,海漄这颗“星星”终于发光了!
在各大平台上,目前收录有《时空画师》专篇小说的《银河边缘009》早已售罄,新加印的书甚至得等到数天以后。这让《银河边缘》的执行主编戴浩然有些兴奋,又有些惶恐:“我们只是一个日常成员不过三五人的小小项目组,且每个人都有自己另外负责的项目,但想不到如今我们也能孵化出一个‘雨果奖’得主!”
而在《时空画师》编辑田兴海看来,海漄获奖却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众多中文科幻作家中,海漄的行事和行文风格都挺“特别”。
比如他格外自律。田兴海除了对接海漄,也对接其他的一些中文作者,他告诉记者,科幻作家群体里全职写作的非常少,大部分人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因此难免会有拖稿的情况。“但海漄几乎从不拖稿,每次我们在聊好构思和创意后,他就会开始写。一旦开始,基本上就会按照交稿的周期进行创作。”田兴海透露,海漄的工作属于“996”类型,经常很晚才下班,可即便晚上十一点下班,他也会坚持写作,哪怕只有两百字或五百字,也从未中断。
此外,在田兴海看来,海漄的作品风格也很明显。“他喜欢找到真实感。比如通过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谜团,再用科学逻辑和想象来解释这个谜团。”比如《血灾》,聚焦雍正时期的“血滴子”之谜,试图用科幻故事引出“血滴子”是什么;《龙骸》,则是用想象试图解释中国“龙”是否存在,为什么“龙”会飞这件事;《时空画师》则是以《骷髅幻戏图》和《千里江山图》为灵感,串联起赵希孟的故事……
田兴海告诉记者,之所以海漄的作品会呈现这样的风格,是兴趣和写作习惯结合的产物,“他的阅读趣味是看历史故事和志怪小说,比如《幽明录》《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也喜欢看纪录片,还有《三国演义》之类的剧。因此在经过长期的写作探索之后,他才选择了用历史来讲科幻故事的路线。”
《时空画师》的诞生也同样离不开海漄日常对历史的关注。有一天,田兴海在与海漄在微信上聊天时,突然收到了一张图片——《骷髅幻戏图》。《骷髅幻戏图》是南宋李嵩创作的一幅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画面中,一个应是流动的携家带口的提线木偶(傀儡)艺人正在进行一场演出,旁边是一个被逗弄的婴孩。整个画面祥和欢乐,毫无惊怖之色。“在海漄给田兴海分享时,他说道,自己有点想以此为灵感,写一篇小说。
“当时他给我发来那张图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也感受到了他的创作冲动。我们开始讨论为什么一个宋代画家可以画这样的图,其中有什么故事,和可以挖掘的地方。”在挖掘的过程中,海漄发现画作者李嵩本人的经历就很有意思:李嵩少年时为画院画家李从训的养子,绘画上得其亲授,后又成为画院待诏,历经三朝,他喜欢画下层百姓的生活,同时在他后期画作《观潮图》《西湖图》中,又通过描绘临安的空洞无人和凄迷风光,表达了对南宋政治的失望和即将覆灭的预感,而这些故事都与《时空画师》中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不谋而合。
田兴海自己也是一名科幻小说创作者,并已发表20多篇作品。他告诉记者,科幻作者最大的共性,就是都拥有一颗不曾磨灭的、对世界的好奇心。“其实人的本性里就有对世界的好奇,但在长大进入世俗生活后,很多人的好奇心会消失。但科幻作者是一个会小心翼翼保护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群体,当他们看到一个好奇的事物后,甚至会生发学习的欲望,去试图用科学去揭开谜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过程就像推理,很符合科幻的审美范式。而海漄的作品正是融合了历史、科幻、推理的元素。”
入围提名最多一次:
中国科幻需要更多突破尝试
继刘慈欣之后,再次有中国作家获得雨果奖,这让不少中国科幻爱好者感到振奋。当然,这意味着中国科幻在世界科幻文学中的一大进步;但对此,田兴海仍保留着一份属于科幻人的“理智”。
田兴海透露,与“星云奖”的专业评审机制不同,“雨果奖”属于大众评审机制,“是由全球‘雨果奖’会员共同投出来的,如果你花300元付费购买‘雨果奖’会员,你就可以参与投票。”为了能够凸显雨果奖的“国际化”气质,每年在选择入围作品时,“雨果奖”就会格外鼓励一些具有民族元素、民族特色的作品。今年是“雨果奖”第一次来到中国举办,因此一方面得益于东道主身份(“地利”),更强调中国元素(天时);另一方面此次参与投票的中国读者也较多,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体为海漄的读者(“人和”)。因此在最佳短中篇小说中只有《时空画师》这一中文作品入围的情况下,它也成为最有可能获奖的作品之一。
占据天时地利的,还有许多其他作品。记者得知,今年的雨果奖评选,是有史以来“非英语”会员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评选,也是中文作品和非英语作品入围最多的一届。翻开今年“雨果奖”中的获奖及入围名单,你会发现不少中国创作者的身影:如获得“最佳职业艺术家”的画家赵恩哲、“最佳粉丝杂志”《零重力报》、入围“最佳短篇”的作者有4名中国作者;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由八光分孵化的《中国科幻口述史》此次也入围了“最佳相关作品名单”,杨枫本人则是凭借八光分出品的《银河边缘》中文版入围“最佳短篇编辑奖”。
“但是在最佳长篇里,今年没有中国作品入围。”田兴海说,相比起中短篇小说,写长篇更像是是一种体力活,对创作者的精力要求很高,不仅是因为创作时长更长,同时对写作者的案头准备、结构能力以及人物故事情节的规划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要求更高。
这些似乎也印证了一个事实:只有当中国有了存在感,文化上才有话语权;且中国科幻若要继续成长,还需要更多的读者群体和创作者群体,也需要科幻人做更多尝试和突破。
“对此我们还是很期待。以海漄为例,从两三年前他发了一系列短篇之后,我就开始催他写长篇了。前阵子交流,得知他的长篇现在已经写了三万多字,同样会是一个和龙相关的故事。希望明年,这部作品可以和读者见面。”田兴海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程依伦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程依伦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