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千里江山图》一出版即有争相阅读之景象,看过的人大多惊讶,“谍战、悬疑、英雄主义,怎么也没想到这些词有一天会用来形容孙甘露的作品”。这种变化,就像抽象深邃的普鲁斯特突然有天觉得,像大仲马那样单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挺好。

2021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出版介绍中,《千里江山图》“画风突变”。所有人都有点蒙:一个关乎青绿山水、十里春风的故事,怎么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图景?这一次,“千里江山图”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撤离的行动计划。主角陈千里如同侦探,穿引长卷全景,又见证图穷匕见;行动小组的成员,充当长卷里一帧一幕,以传递式的牺牲换来真相的拼图。他们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乱世大步行走,在至暗时刻,以肉身直面生与死的钢刃。
为了还原1933年那一个多月的历史图景,孙甘露排出了一张时间表,“阴历的、阳历的,以及在这前一两年上海是不是发过大水,包括当时的报纸广告”。小说中的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是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都是他结合历史和现实设计的。那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萧伯纳下榻过的华懋饭店……在这实打实的地图上,主人公们虚虚实实地出场,请读者享受猜谜的乐趣 :女作家凌汶身上有丁玲的影子吗?转移“浩瀚同志”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重要一环,他到底是谁?

这是孙甘露的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他讲起小说里的一个细节,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待接头,“我查过当时《申报》的广告,说意大利的一个歌剧团在这里上演歌剧,但是剧目被我换成了《图兰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百姓饭桌上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孙甘露塑造了一个别样的上海,没有旗袍、酒吧、咖啡厅的摩登,没有纠结、煽情、撕扯的市井,那是一个明亮、澄澈的空间,革命、理想、信仰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血肉交融,彼此辉映。
小说最后,陈千里目送着自己的弟弟和战友们走向敌人。不用再多说什么,历史自会补足其中热泪。就像他们那一封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 :“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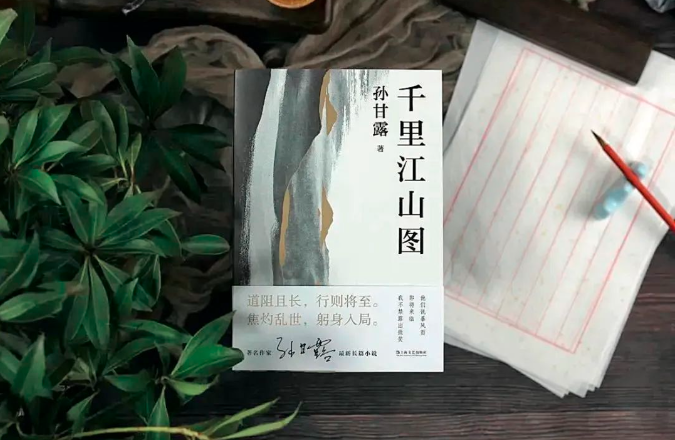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末,昔日的先锋顽童开始抖落技术的衣冠。苏童、余华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走俏文坛,获得可观的市场效益;格非转入学院后写作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在201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先锋试验田里似乎只有孙甘露流连忘返,固执地保持着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
在某种程度上,孙甘露还过着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活,从而使这趟“上海流水”没有并入当代都市生活的现实洪流。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一个人的上海。时代正在改变主题,大众文化兴起,消费主义弥漫,“坦率地,负责地,而且是毫不矫揉造作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孙甘露说。他期待在上海发现某些永恒的东西,希望它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城市”。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或许就在此时来到他的笔底。如同毛尖所说,先锋时代的孙甘露,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翩翩少年,背对观众,拒绝历史。世纪转换,这个男人转过身来,他叫陈千里,“不仅有真名实姓,有确凿身世,有组织关系,有兄弟女友,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这个男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都掷地有声,都进入历史。”

孙甘露的语言是玲珑的、别致的,充满了梦的呢喃,不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它们都有动人心魄的美感,且听——
“与此同时,在远方山脉的另一侧,一些面容枯淡的人预言:一切静止的东西终将行走。于是,树开始生长。平原梦想它们褪去了干草和瓦砾的遮掩,向临近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开始吟唱追忆的歌曲。”
“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种透视的方式向深处延伸。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它的扉页上标明了几处必读的段落和可以略去的部分。它们街灯般地闪亮在昏暗的视野里,不指示方向,但大致勾画了前景。它的迷人之处为众多的建筑以掩饰的方式所加强,一如神话为森林以迷宫似的路径传向年代久远的未来。它的每一页都是一种新建筑。”
孙甘露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也是始终坚持多元化创作试验的作家之一。他始终守望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和遥远的未来。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通讯员:陆文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