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生命在这里逝去,也在这里延续。”
“你有你的朗读者,而我只是一个摆渡人。我们终会上岸,无论去到哪里,都是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
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的《摆渡人》治愈过无数人的心灵,灵魂摆渡人崔斯坦也给每个读者的灵魂注入了一种重生的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医院里,其实也有一群这样的“摆渡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医院里重复着一项平凡而伟大的工作——那就是送逝者最后一程,让他们体面、有尊严地离去。
他们中,有ICU或抢救室里的护士,有负责将遗体从病房运送至太平间的管理员,有负责器官捐献的OPO工作人员,还有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做哀伤辅导的护士……
今天是清明节(4月4日),由广州日报健康有约和广州日报视觉部倾力打造的“医·记录”全媒体产品重磅上线,第一期四集“天堂摆渡人”系列全媒体纪录片也将震撼发布。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天堂摆渡人”的故事吧!

故事一:
“守护好逝者的最后一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人物: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综合病区护士罗稔、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ICU护士李晓燕
护士嘛,不就是量体温、扎针、发药……但其实,他们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角落”,那就是送走那些用尽全力也没有抢救过来的病人——患者走了,她们要拔除病人身上的各种仪器、插管……帮逝者清除血迹,整理仪容,让他们可以体面地跟亲人告别。25岁的李晓燕和27岁的罗稔便是其中一员。
经常目睹生命的更迭,让这些年纪轻轻的姑娘,在娇滴滴的柔弱外表下,锻炼出一颗最悲悯却又最通透的心。
家属哭的时候,我也会哭
27岁的罗稔,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经10年了。
穿着白色护士服站在你面前,一副娇俏可人的模样,可是一工作起来,你不用怀疑,她就是个“老手”,熟稔而麻利。

最开始的时候,她在胃肠外科做护士,那时她还不到18岁。
“病人去世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们整理仪容换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刚开始还是很害怕的。”
第一次接触逝者的情景至今让她记忆尤新。
“当时是下午3点,我去接班,就听说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刚走,我要和另外一个护士去给她整理。当时老奶奶还在抢救室里,抢救室外家属哭得惊天动地,身在这种氛围里,我很害怕,整个人都是懵的,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罗稔说。
护士长看出了她的害怕,就跟她讲,“不用害怕,你是在帮别人做好事,让她们干干净净地走。”然后,护士长亲自带着她去到病房,给老奶奶整理仪容换衣服。
护士长做这些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整个人很肃静,用拧干的毛巾仔细地擦拭老人身上的污迹,擦完了又帮老人换衣服,换好衣服用手把褶皱一点点地抹平,那个场景至今深深地烙在罗稔的脑海里。
“我跟着护士长做这些的时候,眼眶里一直有泪水,但是不敢哭出来,只是小声抽泣。”如今,她还是眼皮子浅,家属哭的时候,还是会跟着流泪,红着眼眶做工作。


爸爸说,你辞职吧,我们养你
“我爸妈是两年前才知道我需要做这些的。”死亡总是一件让人们讳莫如深的事,所以罗稔从来不跟别人说这些。在一次和父母聊天时,罗稔不小心提起来,妈妈一听可心疼了,爸爸说,“当护士太累了,经常要熬夜上夜班,还要接触死人,要不,闺女你就别干了吧,回来我们养你!”
罗稔笑着说,18岁的时候我都没想过离开,现在更不会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会害怕,有些不愿意做,但是慢慢地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人情味,守护好这些逝者的最后一程,保留他们最后的体面,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接触逝者多了,罗稔不再害怕死亡,真正让她感到极为无力的,其实是“死亡”背后的故事。每一则短暂故事的背后,都是一段很长、很沉重的人生。
“7年前,我送走一个70多岁的老伯,当时在医院里一直照顾他的阿姨不是他的原配,而是他后面再婚的老伴。老伯的子女和后妈关系不是很好。但我们都看得出来,阿姨对老伯的照顾非常用心,但子女就老在挑刺,阿姨非常委屈。”罗稔说,平常在病房的时候,护士们就会经常安慰阿姨。
最后老伯走的时候,阿姨强忍悲伤,一定要自己给老伯擦身换衣服,坚持送老伴最后一程,而子女却在外面争争吵吵,开始讨论遗产问题。“我们答应了阿姨的要求,一直默默地陪伴她。阿姨要给老伯穿上7套衣服,到最后,老伯身体发硬,衣服已经很难穿上了,但我们一直尽力地帮助阿姨。”
这些最真实的人间百态,让年轻的罗稔见识到了最真实的人性,也让她对人生、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我们不是在装饰死亡,
而是在抚慰生命
25岁的李晓燕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经4年多了,待在心脏外科ICU两年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她见证了太多生死。
“进来这里的病人,很多病情都很危重,难免遇见活生生的人进来,抢救几个小时,最后冷冰冰地出去。”
刚开始来心外科时,见到这么多泵还有呼吸机、ECMO,以及各种没有见过的仪器,李晓燕说自己“很懵”,慢慢地干了半年多后,她就适应了各种危急情况下的各种压力。

第一次面对抢救场面,是她独立上班不到一年的时候。
那个病人已经处于紫绀、呼吸衰竭状态,老师带着她给病人插尿管、胃管等,大家忙碌了1个多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22岁的她走出ICU时不禁崩溃大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从我手里走了,觉得特别遗憾和难过。”
“在我手上的病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健健康康地走出去。很多人说你们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见惯了生死,应该很冷漠了,我说恰恰相反,我会换位思考,很多我护理的病人我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如果是亲人走了,你不会伤心吗?特别是有些病人,跟我们相处久了,都很有感情,他们去世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难受呢?”
“一个50岁的大叔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半个月,我把他当父亲看,之前他还说等好了要请我们吃饭,但没过两天,他病情突然恶化就抢救不回来了,我们都很难过。我在想,这要是我的父亲,该有多遗憾啊,我还有好多愿望都没有跟他做呢!”
那时她倍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也清晰地感知到,由生迈向死,有时仅仅只是一瞬间。
所以,她对病人更多了一份爱心,对家人更多了一份耐心,很多想和家人一起做的事情,想起来就赶紧去做,“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也有遇到家属不能理解的时候。
刚抢救过来的病人还在监护室里,家属就要求她将手机拿进去给病人,李晓燕坚决拒绝:“病人的身体还很虚弱不能看手机,另外电子产品也会影响里面的仪器。”可是家属不理解,责怪她,说,“你不配当护士。”还投诉她,但李晓燕还是坚持这么做。事实上,病人下半夜就出现了一过性的室速室颤。
“很多时候我们付出了,病人和家属不一定能感受到,反而会误解你。还是很难过的。”李晓燕笑笑说,但误解就误解吧,该做的工作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病人最终走的时候,李晓燕要把他们身上的各种仪器拔掉,帮他们处理身上的血迹,整理仪容。
“没有人能拒绝死亡,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最平等的。我会尽全力帮她们整理仪容,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因为她们的家属都还在门外等待,期待着见他们最后一面,我所能做的就是让逝者走得更体面,更有尊严。”
“我们不是在装饰死亡,而是在抚慰生命,告诉活着的人——请记住你们亲人最后的样子,然后放下悲伤,带着思念,勇敢继续今后的人生。”
故事二:
10年,他为近7000死者提供“中转站服务”
人物: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总务部太平间管理员陈迪彪
病床上,最后一缕生命气息飘散,有一群人悄然而至,将遗体妥贴运至太平间暂留,等候殡葬车送往后事流程。
即将40岁的湖北人陈迪彪已经在广州的医院里呆了近10年,为近7000位死者提供了“中转站服务”,说起太平间管理员一职,他说“要有一颗尊重的平常心”。最大的职业感悟是,死亡能拉近所有的不平等,生命脆弱,平安健康值千万金。

无数个“35分钟”
电话响起,ICU有一名患者救治无效去世,陈迪彪与两位同事花了15分钟穿好防护服,先给冷藏冰柜消毒杀菌,再推着遗体载具——转运推车出发。
沿着专门通道赶到床前,与护士、家属初步沟通后,三方核对死亡证,细心用空信封装好;核对病床号,检查遗体,将手术创口在死亡证后标明,再一次三方见证并签名确认;等家属暂离,陈迪彪带着同事进入遗体料理环节,包括穿衣或将病号服换成自己衣物,使用夹板、尸单等最大限度恢复生前体貌,然后用裹尸袋打好包,转移至遗体载具,特殊材料用的裹尸袋可防体液血液泄漏。
准备妥当后,家属与他们一起将遗体送往太平间。
他们使用的是隐秘的专门电梯、特殊通道,两人推车,一个在前开路,“麻烦让一让,特殊运送……”这样的话撒在一路上。




到太平间,门、柜、抽屉的锁分别被团队三人打开,将遗体转移至冷藏冰柜,在遗体接运登记表填妥日期、科室、太平间接收时间、死者姓名、性别、年龄、死亡证编号、是否有遗物后,家属签名确认。陈迪彪拨通墙上公示的广州市殡葬服务指引上的电话,请家属接听,通过殡葬车来接运,“家属不能慌,也别信什么代办,指引上流程明确,拍下来,一步步办理就好了”,他安抚着说。

一般接运车6~8小时才来,家属不用等在医院,“您看,这里全是摄像头监控,三把锁是三个当班的人分别拿钥匙,别担心遗体损伤或遗失。”陈迪彪解释,接的车来了,还会在监控下再核对,登记来接收的人、车号。
这样的流程下来,陈迪彪跟同事与每位死者平均“接触”35分钟左右,长年累月默默地提供着从病房到殡仪馆间的“中转站服务”。
“我予以尊重,他们教我珍惜”
2012年转业至今,陈迪彪在医院里呆了近10年,接收、送走了近7000具遗体,他直言,开始时对“太平间管理”这份工有好奇,坚持至今“觉得自己挺棒的”。
“送死亡者最后一程,有人忌讳,但总得有人做不是?”陈迪彪回忆,当时战友们商量着成立了物业公司,自己先是在另一家医院,2018年通过招聘,进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太平间。
整整从业三年后,他才敢告诉妻子“真相”,之前一直只说是“医院保安”。他至今还记得,妻子愣住了,停了一会才问他:“要擦身吗?要帮换衣穿衣吗?有没有做好防护……”他连忙将医院感染防控培训、系列管理制度等所有的全“交代”,妻子还追着他叮嘱:“你是共产党员,又曾是战士,可千万不能收红包、黑钱!”
“她真是贤妻,对吧?”陈迪彪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其实,不用妻子叮嘱,陈边彪与同在省二医的近30位同事们都深有感触,一句话就是:“我予以尊重,他们教我珍惜”。
每趟“中转服务”,他们总是快速出动,为的是减少对其他病患的影响;行事利落而细语,体贴着正陷于刚失去亲人的惊惧悲痛里的家属;就连穿衣,除非家属强烈要求,否则全程家属不动手,因为毕竟遗体衣物穿脱难,划损后失却尊重。
“尊重”二字,是陈迪彪们坚持予以新逝者的安息礼物。偶尔会有家属要求在太平间存久些,好让最亲的人来见最后一面,陈迪彪非常耐心地沟通:太平间冷藏冰柜是零下18度,而不是殡仪馆冰柜的零下三四十度,三五天遗体就可能产生青斑,对逝者而言既失尊重也不体面。
“服务过”无数新逝者,陈迪彪最大的感受是生、死是最大的平等。有一位逝者,生前是做企业的老板,拼事业却突然猝死,心梗加上脑梗,花了很多很多钱想抢回命却未果。还有一位10岁的女逝者,普宁人,因为癌症折磨,尽管家人带着她辗转求医,最后还是少年离世。更别说看到很多突遭车祸等意外的人,可能连一句话都没留下,亲人们哭断肠。
“新生到这世上,没人知道这辈子喜悲多少;从这世上离开,没人能带走一丝一毫。”陈迪彪说,所以人生在世,与金钱、权势相比,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不逼着孩子光顾着学习,欢度童年时光;家人间好好相处,享受在一起的世界;陈迪彪甚至为家人订制了一套身体锻炼方案,自己带头日日锻炼一小时。
“近10年,经手接送近7000人,我小时候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么多人死去,可生命就是如此脆弱。”从医院隐秘的角落——太平间走出来,讲述“生命中转站”的故事,陈迪彪最希望,在世时,人人珍惜生命,爱惜身边人;离世后,人人尊重逝者,那是生命在这世间最后的形态。
故事三:
为早逝的小生命送行,给准爸妈留下希望
人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
“亲爱的小宝:很抱歉没能把你迎接到这个世间,让你健康成长。爸爸妈妈真的尽力了!希望你和大宝一起在世界的另一边过得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们!”
小小的心形卡片上,写着几行朴素却字字泣血的寄语。这是一对年轻父母对未及出生便逝去的宝宝最后的祝福。不久后,它会陪伴着早逝的小生命,一起化为青烟,带走父母的不舍、哀伤,留下对生命的渴盼和对生活的希望。
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病房,近三年来已经有一百多位父母经过护士们的“哀伤辅导”,完成对夭折胎宝宝的哀悼和告别仪式。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历过多次保胎失败,备受打击,甚至有人曾因绝望、无助而自残。
“与其说我们用‘哀伤辅导’来治愈悲伤的准爸妈们,不如说是他们在震撼我们,治愈我们,让我们更加尊重生命。”首创这项护理服务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在受访时几度落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在受访时几度落泪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妇产科护士长翁雪玲在受访时几度落泪
翁雪玲说,对病人予以人文关怀,是秉承了医院的一贯理念,给早逝的小生命和他们的家长一个体面和温情的告别,让他们释放哀伤走出悲痛,过好接下来的人生。
十多次失去宝宝,
这位妈妈感慨“分娩间太冰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生殖医学、保胎技术享誉华南地区。在妇产科病房的产前区里,经常住满需要保胎的孕妇。尽管保胎成功率有80%,但仍有不少患者属于复发性流产。有些孕妇历经千辛万苦,怀孕到七个月,却依然挽留不住腹中脆弱的宝宝,身心受到巨大打击。
“来住院保胎的准妈妈中,时常有‘熟面孔’。有的人甚至流产十多次,有的人不惜以命相搏,冒着大出血的风险,最终还是保不住孩子。”从事护理工作30多年的翁雪玲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人间百态:有的人第一次来,身边有老公和婆婆相陪;渐渐地,再到产科保胎的时候,就变成孤身只影。

曾有一个十多次失去宝宝的妈妈,流着眼泪跟护士姑娘们说:“分娩间里太冰冷!” 其实,她是因得不到亲人的理解支持和陪伴,才会格外孤独、脆弱。同为女性,产科的护士们常常对这种悲痛感同身受,为她们心疼不已。
其实,失去宝宝的打击对爸爸们同样巨大,但男人们往往不懂表达,也不会及时地宣泄自己的悲伤,恰当地给妻子情感上的支持。”翁雪玲和同事们见过一个“准爸爸”在再次失去宝宝后蹲在楼道里无声地哭泣,有人经过时又迅速地站起身来掩饰悲伤。
翁雪玲说,如果他们不能从哀伤中走出来,就不能真正地与自己和解,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最后的尊重:“把他们当成健康的新生儿”
2018年,一桩意外的发生,让翁雪玲和同事们深受触动,决定为14周以上安胎不成功的妈妈提供公益的“哀伤辅导”护理服务,“在她们最难的时候拉她们一把,劝劝她们,抱抱她们,让她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

因胎儿停止发育而接受流产手术的孕妇一住院,护士便会对其进行“哀伤辅导”。如果遇到孕妇哭泣,护士便什么都不说,静静地握着孕妇的手,轻轻抚摸肩背,默默陪伴。等她稍平静时再做进一步的安慰。“我们会问她需要哪位亲人进来陪伴分娩,告诉她我们能帮她们与宝宝告别,可以拍照留念,爸爸妈妈有什么想和宝宝说的话,都可以写在爱心卡上。”翁雪玲说,为了让孩子爸妈充分宣泄悲伤,护士会尽量满足他们的心愿。
对于早逝的小生命,护士们也会细心地为他们清洁身体,穿上预先准备好的新生儿服装,包上小包被,放进特制的盒子里,男孩是蓝色的盒子,女孩是粉色的盒子。随后由孩子的爸妈与孩子进行最后的道别。

这些在子宫里夭折的胎宝宝,毕竟与正常新生儿不同:有的属于致命的畸形,有的是水肿胎,有的肢体残缺……年轻的护士们进行护理操作时,要面对心理上的巨大挑战。然而,她们每一次都会小心翼翼地进行护理,把他们当成健康的新生婴儿,给他们最后的温柔和尊重。
“我的同事们都很年轻,很多人还没有当过妈妈。看到她们为宝宝和他们的爸妈所做的一切,我时常感动得流泪,对她们的无私付出充满感谢!”翁雪玲说,这些努力,让医疗护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
“拥有你的七个月,很幸福”
“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要让准爸爸参与进来,不仅支持准妈妈,也帮助他们释放自己的哀伤。”翁雪玲说,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孩子爸爸该如何安慰孩子妈妈,护士们也会耐心地指点。
曾有一个有过多次流产经历的妈妈,怀孕七个月时再度遭遇不幸。孩子的爸爸一直默默支持着妻子。护士们回忆,他坚持给去世的胎宝宝留下脚印,“要让家乡的亲人知道,我是有孩子的!”他在给孩子的卡片上写道:“宝宝,拥有你的七个月,爸爸妈妈很幸福!”孩子被送走火化的时候,他早早地守在产科门口,想要再看孩子一眼。最后,他给送走孩子的护士们鞠躬。
这样的“哀伤辅导”和对小生命郑重的告别,让不少准爸妈的心灵得到治愈,增进了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有个准爸爸在妻子又一次流产之后,激动地抱着妻子喊:“老婆,你受苦了!我们不再要孩子了,这辈子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孩子爸爸的参与非常重要。
孩子爸爸的参与非常重要。
目睹这样的场景,翁雪玲和同事们会感到特别欣慰。
“有人关爱的分娩间,不再冰冷。我从没想过,在这里还能感受到这么温暖。”一位多次流产、曾经每日以泪洗面的孕妇,接受过“哀伤辅导”后,在出院时跟辅导她的护士感慨道。同样是这位孕妇,最近经过两次保胎,终于平安地生下宝宝。
翁雪玲说,每一次心碎的告别仪式之后,“我们最欣慰的是接受‘哀伤辅导’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们能走出忧伤,迎接新生。毕竟,人生漫长。”
故事四:
“让善良的种子发芽,当生命延续的桥梁”
人物: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刘永光
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始于2012年,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珠江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办公室也是成立于这一年。作位一名上世纪90年代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器官移植科工作的医生,刘永光也是在那一年上岗成为一名OPO(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的。OPO协调员就是去和逝者家属“谈那件事”的人。
从事了将近十年的OPO协调工作,他见过了很多的生死,见过了很多生死之间的人情百态。刘永光说,从哲学的层面上讲,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都是“向死而生”,“而我们的工作,是去诠释一种生命的延续,做好生命的“摆渡人”,作为桥梁,去传递信息,促成逝去的生命获得新生,帮助可能逝去的生命得以延续新生。但我们并不是去‘说服’,只是去让原来就存在的善良的种子发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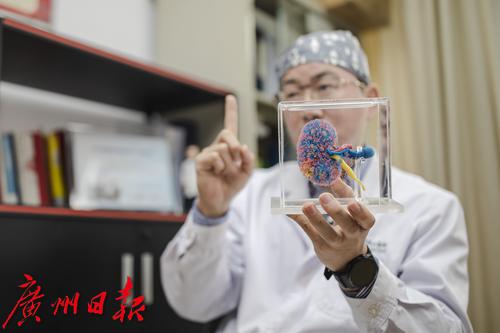
“我只想站在街头,
感受一下孩子眼睛看过的这座城市”
对于逝者的亲人来说,逝去的人能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延续生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慰藉,这是他们同意捐出亲人器官的一大重要意义。
刘永光对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这个男孩因为某种脑疾去世之后,父母签下同意书,捐献了他的肾脏和角膜,孩子的骨灰撒在了珠江口,因为他生前就喜欢玩,希望能“到处去走走”。这件事瞒住了孩子年迈的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爷爷还是知道了。这位爷爷找到了刘永光,说:“我知道你们有规定,不能透露器官受者的信息。但是医生,求您能否告诉我,他们在哪个城市?我想去到那座城市,在街头站一站,哪怕只是感受一下,孩子的眼睛如今看到的街景。说不定身边走过的哪一位,就是他……”
最后,爷爷如愿知道了那座城市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没有,不过走之前,老人家也在珠江边站了很久。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我们难以拒绝。”刘永光说。
观尽人间百态冷暖 心中仍有温情力量
OPO协调员做些什么?要在恰当的时机,及时、准确地将“脑死亡”是怎么回事向家属解释清楚、告知家属可以选择为亲人捐献器官、解答家属的各种疑问……但他们的工作,又不仅仅是在医院、在病房和办公室动动嘴皮子。
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已经见惯了各种生死离别,协调OPO的工作则让他们接触了各种各样家庭的人情冷暖,有时候也包括全国各处的奔走,比如为了取得一位身在异地的直系家属同意,临时连夜飞到另一个城市。大多数能够接受器官捐献这件事的家庭,还是充满了正能量的。但因为器官捐献有特殊性,必须征得逝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所有一级亲属的一致书面同意,哪怕有一位反对,都是一票否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员会接触到逝者的各种家庭关系,各种各样的人。
这些逝者中,有夭折的幼儿,有意外事故中脑死亡的年轻人、家中的顶梁柱,有来自遥远国度的外国友人,甚至也有他朝夕相处的年轻同事……于是,协调时面对的可能是悲痛的妈妈、无助的妻子、哭泣的孩子……
刘永光说,有的人会情绪崩溃,会反悔,有的人可能麻木,有的人依然不能接受亲人逝去的事实;还有的人,可能有种种的怀疑,甚至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各种能想到不能想到的情况和关系,都需要协调员去处理、去协调、去解释、去安抚。
曾经有一次,为了协调一个孩子的器官捐献事项,刘永光的同事连夜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希望获得孩子妈妈签署同意。这位离异妈妈已经很多年没有跟孩子在一起,对远在广州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充满了排斥、抗拒的敌意,协调员多次电话沟通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勉强同意由协调员前往她生活的城市,直接在机场签署同意书。当协调员见到她的时候,俨然发现她高度戒备地带着好几个牛高马壮的男性亲友。
“估计是准备一言不合发现我们是坏人,就要马上打起来了吧。”当然,最后冲突没有发生,协调员顺利取得了她的签字,又火速回到了广州。
心路:
从内疚到坦然 尊重每一个人的任何决定
也不是所有的协调都能获得成功。从2012年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以来 ,截至2020年,珠江医院共有299例捐献。刘永光说,从筛选可能合适的捐献者,到和他们接触,到最终同意捐献,OPO协调员一年可能要接触数百近千的个案和家属。而近年来每年大概成功捐献的有70例左右,大概每谈话4到5例,会有一例最终能够达成捐献。“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刘永光坦言,“一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会觉得自己在‘做恶’,毕竟那时候整个社会人们普遍不太能接受这件事,而且面对至亲的离去,已经是很残忍的一件事了,你却还要去讲“器官”,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急诊科收治的一名脑出血病人,在医务人员竭力抢救之后还是最终被判定为脑死亡。“刚开始见到家属,总是觉得这个时候人家最痛苦,自己在说捐献感觉有点像是在别人伤口上撒盐,三个多小时,就在家属面前转来转去,张不开嘴。”
“后来慢慢习惯了,也更明确一点 :一个人走了之后,如果他的器官还能挽救得到别人的生命,应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归宿。我们要说服别人,首先得说服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这件事不能急。虽然那边病人正急切地等待着救命的器官,但也必须慢慢地让逝者的家属了解脑死亡是什么情况,他们还可以为自己逝去的亲人做些什么。”
如今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到2018年,我国器官移植例数已经是全球第二。刘永光说,这些年来,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观念有了巨大改变,“一方面我们OPO工作人员自己对生死的感悟,确实有了很多不一样之处,另一方面老百姓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但在生死面前,其他的事都不算什么。每个人都有机会直面生死,面对生死,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而不是纠结于‘做不到’的焦虑。我们不会对‘成事’进行过高的预期,也不会因为家属拒绝就感到特别遗憾,而是更专业更客观地去面对每一位逝者家属的抉择,尊重他们的决定。这种程序上的正义才能保障我们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
统筹策划:翁晓鹏、张伟清、黎蘅、陈向军、张青梅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青梅、何雪华、任珊珊、周洁莹 通讯员张灿城、周颖怡、朱健、黄怡辛、林伟吟、张阳、黄睿、伍晓丹、韩羽柔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铭曦、陈忧子、苏俊杰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铭曦、陈忧子、苏俊杰
剪辑/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陈铭曦、罗知锋
海报设计/周振丰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津